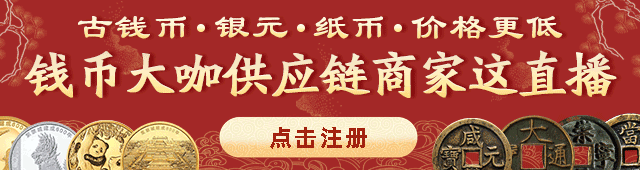镜像理论视野下的纽约画派与后现代艺术
人的大脑和身体如何构成一个主体?这是一个复杂、连续的过程,一个与心理有关的过程,一个社会化的过程。雅克·拉康(Jaques Lacan)在他的著名论述中指出,这个过程的开始,就是婴儿在镜中认出自我的形象,并把自我想象成一个整体。他假设,在这个初级的前社会(presocial)阶段过后,马上就是一个融入社会的阶段:人进入象征界(Symbolic)[3],在接受语言和法律的统治之后,开始被他者和所遇到的各种差异反复塑造,从而成为一个分裂的主体。作为一个社会过程,主体的形成会因为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文化环境而有所不同,并且,其形成过程还会受到意识形态的渗透。

婴儿与镜子
主体在进入象征界后,会继续运用镜像去“理解”或者想象自己的样子。它会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或者一个整体,然后沉浸在自己的美丽或精巧之中,还有它所表现出来的各个侧面、它的脾性、它内在的心理机制。在某些情况下,简单的镜中形象并不足以支撑复杂的自我认识,这时候,其他的视觉媒介会代替镜子。比方说,绘画,就可能成为一个人们中意的领域。人们会在绘画中寻找自我的核心,并且看到,这个自我的复杂状态和心理活动在绘画里得到上演。绘画的物质载体和某些与话语产生共鸣的比喻,则通过画家对物质的运用,通过创造出虚幻的图形、或者与现实世界相似的图形,可能都会变成一种表达人类自我的媒介。在画面中找到了自我之后,观众可能会被它强烈地吸引,并且把自我投射到画面里,或者,他们也可能会受到画面的询唤。[4]因此,绘画与人在互相认识彼此。观众可能会像自恋的那喀索斯一样,沉醉在自己所看到的形象之中,无法自拔,即使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分裂的、恐怖的、脆弱的自我,与那喀索斯迷人的水中倒影相去甚远。

水中的那喀索斯
本书认为,出现于二战期间以及二战结束后的纽约画派,就受到了人们的这般解读。当时的美国人普遍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恐怖的世界,这种看法就被一张玻璃镜真实地反映出来。现代的那喀索斯之所以注意到那些展现自我的表现形式,并非出于爱恋,而是出于恐惧、焦虑和绝望。他们所看到的自我,要么是一个内心矛盾的古人类,身上隐藏着令人害怕又深不可测的原始冲动,要么,就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可怜虫,受尽自然与命运的摆布。而这些形象,绝非某种迷人的个体。这些自我形象就栖居在被我们称为抽象表现主义的作品里面。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那些作品呈现出了一些独特的视觉隐喻——这些隐喻体现了艺术家纠结的创作过程、性别对立、原始元素的贯穿、能量的流动、无意识、控制与时空、空间中的罗网,等等——它们恰好符合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话语对自我和身份的定位。没有一种隐喻能够完全概括抽象表现主义画作;相反,那些最受欢迎的作品其实超出了单个隐喻的局限,并且可以在人们的众多修辞之中自如穿梭。这也就是为什么抽象表现主义能够展现出复杂的现代主体。

德·库宁,女人
但是,正如那喀索斯会渐渐憔悴,因其单相思无法得到回报,或者说,因为他只是在顾影自恋,所以,现代人也无法从其狭隘的关注当中获得满足及深刻的体验。抽象表现主义的绘画如同那喀索斯张望的湖水一样,只是一面失真的镜子[或者,用波洛克1941年的一幅绘画标题来说,它们构成了一面“魔镜(magic mirror)”]。那喀索斯在水中看到的,是一张美丽的脸;水面无法告诉他,他所谓的美丽只是一种过高的自我评价,也无法告诉他,水面上的人并不是他臆想中的女神艾蔻(Echo)——在向那喀索斯表达爱意又被拒绝之后,艾蔻已经幻化成一种没有实体的回声。[巧合的是,波洛克在1951年将一幅作品命名为《艾蔻》(Echo)。]同样,抽象表现主义画作只是向现代人呈现出了一种狭隘的、心理意义上的自我;显然,当时人们所看到的身份,并非是某种身体形象,或某种社会地位,而是不同层面上的人类心理机制,以及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激烈争斗。这种虚构出来的身份是对旧有身份模型的改造;它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令人痛苦的历史事件向掌握霸权的意识形态施加了压力。这种新的自我,对占据主导的意识形态显得很“友好”,因为它能在最大限度上确保后者的基本范畴、信条和假设得以维持。反过来,这种结果又成为新自我得以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纽约画派的作品里,在现代人文本里,观众们找到了自我,塑造了自我,也认识了自我,而这种自我其实是某种意识形态下的主体。正是凭借着绘画和文本,意识形态渗透在自我意识的框架和核心之中。这种对主体性的殖民是霸权意识形态的力量之源,也是推动这一意识形态得到巩固和向前发展的有利条件。在一则知名的段落里,路易·阿尔都塞如是说道:#p#分页标题#e#
主体这一范畴是所有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但与此同时,我想为这句话加上一个必不可少的附加条件:正是因为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有能力(这也是意识形态的特点)把实实在在的个人转化为主体,主体这个范畴才会存在于所有的意识形态中。[5]
为了令人信服地呈现出现代人的主体性,纽约画派的艺术家们也把自己构建成为意识形态下的主体,并以此创作出了询唤观众的作品。

杰克逊·波洛克
正如现代人的主体会取代原来之前逐渐衰弱的主体,它自己也在一段时间之后受到了围攻。就在我写作期间,后面的这个过程正在上演,因此本书难以对此作出概述。但从目前来看,在这一过程所发生的10年间,抽象表现主义所表现的主体性似乎开始让不少艺术家和观众觉得,它是一种夸张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存在。一种审视主体的新态度,即我们口中的后现代,开始登场,它最早在贾斯珀·琼斯(Jasper Jones)、罗伯特·劳申伯格(RobertRauschenberg)、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罗伊·利希滕斯坦(RoyLichtenstein)等艺术家那里露出端倪。他们呈现出来的自我没有中心,不存在深度,也不存在内心的骚动——自我在不断重复的图像里,在对现成品的挪用中慢慢消解;它更像是艾蔻,而不是那喀索斯或“现代人”。艾蔻的性别并非无关紧要:我们看到,那些因为性别、种族和性取向而不能认同抽象表现主义的艺术家们在批评抽象表现主义和引导艺术转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劳丽·安德森(Laurie Anderson)、巴巴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谢莉·勒维恩(SherrieLevine)、安德里安·派普(Adrian Piper)以及辛蒂·雪曼(CindySherman)等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不仅公开批评现代主义倾向于展现白人、异性恋者以及男性的主体性,并且,她们也对这种现象造成了瓦解。

辛蒂·雪曼
有一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那就是,所谓后现代的自我真如其名所示,具有彻底的颠覆性吗?还是说,它其实没有那么激进,也没有那么确定?也许,最明显的变化只在于,现代人已经从他的疾病中康复,已经可以再次将力比多投注于外部世界?现代人话语总是假设,心理先于社会和政治而存在,也决定着社会和政治,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就能明白大概。本书所讨论的现代主义的主体,其实与后现代的主体在许多重要方面是相似的。现代主义的主体可能曾经是一个整体,但是,它却不总是、或者说必须得是统一、集中或自主的。因为在纽约画派的绘画中,人们上演着、展现着对于“创造之神”的废黜。同时,自我变成各种冲突要素的集合,我们便可以说,后现代或后结构主义主体的雏形,就存在于抽象表现主义中。正如拉康、德里达等人发现,弗洛伊德在动摇现代的自我的时候,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抽象表现主义这个盛期现代主义的象征,在一些重要方面预示了后现代的主体性要发展的方向。主体内心的破碎、崩溃,以及自主性的丧失,已经在抽象表现主义的艺术作品中上演。不管我们是否把后现代主义视为一种传承,我们都不能脱离抽象表现主义来看问题,这样只会有失偏颇。那些艺术家们所锻造出来的主体仍然需要得到我们的认识;人们经常看到,抽象表现主义受人推崇,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因此,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便写道:“纽曼可以清晰地描绘出现代艺术家的内心世界,这就像委拉斯贵兹等经典画家清晰地描绘外部世界一样。”[6]#p#分页标题#e#

巴内特·纽曼,谁害怕红黄蓝
本书旨在证明,所谓“现代艺术家的内心世界”有其具体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它一方面影响了这些艺术家,另一方面,也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得到展现。假如我们要继续肯定抽象表现主义的艺术水准,那么,我们必须在考量的过程中重视它的历史特征:它同时参与和拒绝了各种各样的话语框架(这些话语框架既塑造了它,也同时在被它塑造),它既巩固了意识形态的合法地位,同时也对它构成颠覆。假如我们想从研究当中有所收获,我们必须认识到,抽象表现主义进步的一面,其实深深地暗含在其保守的一面当中(有人可能会说,进步的一面被保守的一面掩盖)。此外,正如占据主导的意识形态构建、利用了纽约画派作品当中的新主体形象,后现代主义的自我也证明,它也可以参与霸权的运作,并参与霸权对文化生活的广泛商品化。抽象表现主义的历史,展现出意识形态与政治讨论在文化领域的争论焦点;希望它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不会阻碍以后的文化批评,而是会对它们起到积极的促进。
注释:
[1]本篇译文节选自《重构抽象表现主义——20世纪40年代的主体性与绘画》(Reframing Abstract Expressionism: Subjectivity and Painting in the 1940s),一书,耶鲁出版社,1993年版。全书共四十万字,即将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本文标题是译者添加的。
[2]迈克尔·莱杰,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19世纪至20世纪视觉艺术。毛秋月,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现当代艺术批评理论。
[3]译者注:拉康把个人主体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划分为三维世界:实在界(the Real)、想象界(the Imaginary)、象征界(the Symbolic)。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术语的用法是将形容词名词化,其意义指涉比较灵活,既指界域或秩序,也指认识、性质或功能。实在界,是一种无语言也无前语言的状态。一个人在生命早期阶段,还没有受到语言的影响,也没有受到他者的影响,完全依赖最原始的需要来行动,这种状态就是处于实在界。想象界是镜像和前语言阶段,人在受到他者影响之后,开始把外在的东西与自己的存在建立起一种关系,认识到自我和他人的二分。这里的自我,是错误的把镜像当作自我而丧失了最原始的、你我不分的本我。由于外在的认识掩盖了最真实的本我,人开始脱离原始自然的本我,需要把镜像和镜像外的自己建立起关系。这种状态就是想象界。在象征界,人远离本我的状态,受到各种语言的影响,受到各种外在和内在的复杂欲望的影响,进入到复杂的意识形态之中。拉康的理论艰涩、抽象。译者只是根据已有资料,做了一个十分简要的概括。读者可参见拉康于1953年发表的论文《象征、想象与实在》(“Le symbolique, l’imaginaire et le reel”)。
[4]译者注:“询唤”一词来自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机构和话语“招呼”(hail)人们,邀请人们与它发生某种关联,从而把个人转化为主体。
[5]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BenBrew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171.
[6] Stella, “How Velasquez Seizes theTruth That Is Art,” New York Times, 1Oct. 1989, sec 2, p. 39.
- 上一篇: 谈谈中国画的“空”
- 下一篇: 中国书画市场进入牛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