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过道:杨永生绘画作品简评
杨永生的画是写实的,写实总是意味着两种方式,一个是技术的方式,把客观对象如实地记录下来,这种记录是需要技术的,主要是要再现一个真实的空间,在笔触和色彩的配合下,运用透视的法则,在一个平面上创造出有深远感和立体感的三度空间和体积。在这种选择中,题材往往是不重要的,题材作为技术的媒介,但这种题材只是事物的表象,技术通过表象的真实显现出来,同时也体现技术的价值。另一个是题材的方式,即不将技术作为记录表象的工具,而是记录事实的工具。当然,事实也有表象,库尔贝说过,现实主义艺术是表现事实表面以下的真实。这就是说,技术不在是独立的价值,而是“真实”的再现。杨永生是油画系毕业的,受过严格的写实训练,所以在写实上很自信的。技术上的自信意味着表现的自由,他总是能够把观察到感受到的东西自由地表现出来,把没有绘画性的东西赋予绘画的生命。当然,这还只是表象的真实,也几乎是每一个写实画家的起点,但并不是每一个写实画家都能够进入表象以下的真实。 象的真实到内在的真实是有一个过程的,学院的训练截止于表象的真实,即使是熟练的甚至精湛的技术都不可能自动的达到内在的真实。真正使对象具有绘画的生命还是不够的,只有艺术家自身的生命投射才能使对象获得内在的生命。杨永生的艺术道路并不长,但他从一个掌握了写实技巧的学生到表现事物的内在真实,应该是生活本身给他的启示,甚至是付出了生活的代价才获得的启示。杨永生说过,艺术就像一幕戏剧,艺术家就是导演,每一件作品就是片段。这其实是一个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但杨永生和这个传统还是有区别的。传统的戏剧是演给别人看的,是按照公众的趣味来编排的。他的戏剧是生活的体验,是经历了精神的嬗变后对生活的洞察和人生的省悟,他的戏剧是需要解读的,因为人们不可能像看好莱坞电影那样观赏他的作品。 利文艺复兴的时候有一种说法:艺术是艺术的隐藏。这个意思是说,当一个现实的场景用艺术的手段复制出来后,手段本身要不露痕迹。意大利人相信以透视为中心的科学手段能够不露痕迹地再现客观的真实。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表象的真实总是依赖于写实的技术来实现的,艺术家如果奴隶般地服从于技术,只能制作出没有生命的表象。让艺术从艺术中显现出来,消解如实的再现,杨永生的画中体现为两种策略。其一是表现化,笔触的快速运动与变化,颜色的不协调性,以此形成对客观对象的个人表现方式。其二是图象化,在构图与色彩上都有照片化的倾向。照片化的概念来自日常生活中的摄影经验,瞬间的抓拍场面和罗列式的布局,都是与绘画的理念格格不入的。尽管图象化也是非个性的,但图象与表现结合起来,就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虽然这不是杨永生的原创,但他确实把它发挥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事实上,这还只是杨永生的再现方式,他寻找自己的再现方式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再现本身,而是为了再现的内容,是为了叙事的需要。 在杨永生的作品中,有一组以《灯》命名的系列画。从《灯(一)》来看,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楼道里的灯,昏暗而孤单,伴随着一种凌乱和肮脏。强烈的透视感和有些怪诞的颜色,说明它可能来自一张照片,或至少是有意追求照片的效果。“灯”的下面是一个过道,没灯的时候肯定是一片昏暗。杨永生是想向我们再现一个真实的过道吗?或者是借这个过道来向我们展示他对光的偏爱和表现光的能力?过道本身是非绘画的,如果要表现光感的话,他完全可以画一组特殊光线下的静物或灯光下的人体。“灯”指示着过道,过道是他的一种认知,过道在他的笔下获得生命,是由于他对生命的体验。这种体验的第一个层面是生活的经历,是一个具体的的生活环境,生命存在于这个环境中,也暗示着对生命历程的记录。体验的第二个层面是超越过道作为生活环境的意义,这样过道就具有一种的象征性,它是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它具有生命的意义的价值。昏暗与封闭的过道犹如一个生命活动的场所,杨永生所导演的戏剧都是在这个场所中展开。 由于“过道”的定位,使杨永生的作品都具有象征性。他的作品都有一种真实的荒诞,一种似乎只有在梦中才能出现的场景,无论是《灯光》系列还是《室内》系列,都是一种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杨永生却通过一种真实的制作“伪造”了这个场景。这种真实被两种可能性掩盖起来,其一是绘画性,这种绘画性掩盖了题材的必要性,造型的准确与笔触的魅力似乎使题材无关紧要,表象服从于绘画性的需要。其二是场景的真实性,人物的动作都在自然的状态中,在一个抓拍的瞬间,甚至它本身就是以照片为基础。但这种真实并不等于现实的真实,反而是一种荒诞。对于这些作品的意义只能从整体上把握,用美术史的术语说,它只能作心理的解释,而不是文本的考据。对杨永生来说,这些场景只能在封闭的过道里发生。过道外面是一个阳光的世界,是他曾经那样认识的一个世界。生活的经历告诉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就像人的生活一样,在理性行为的表象下面还有一个潜意识的世界。 这可能就是“过道”的意义,杨永生并没有主动地阐明这种意义,但他的艺术打通了两个世界的关系,这是生活给他的启示。在这个过程中,绘画和现实都发生了变化,我们不能把他的作品看成简单的写实,而应是在他的语言方式中对生命、生活、现实的理解。#p#分页标题#e#
- 上一篇: 迷惘与空灵:谈杨永生的油画
- 下一篇: 热淘典当行,绝当收藏品走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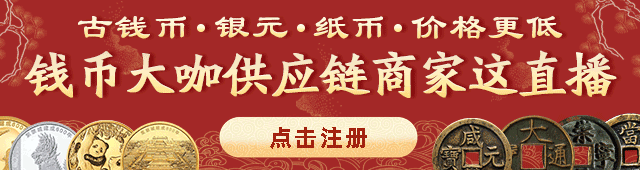







.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m_fill,h_110,w_135/format,jpg/quality,q_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