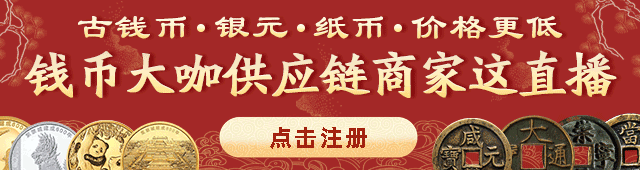诡异的优雅——王斐绘画中的历史和神秘
“……王斐的作品表达了痛苦的存在主义之父克尔凯郭尔式的真谛:人生,无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从个人角度来看,守望未来的同时却又不得不逆向的理解过去……他的作品探究一种与自身精神源泉断割的文化的耻辱,是献给那个消逝世界的挽歌……龟是不朽和长寿的图腾,正是中国人在它的背上刻下了中国最早的文字。它也用来占卜。王斐饲养的乌龟们探出头,谦和地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无论是关于审美还是文化;画家本人也随时牵挂着这个有血有肉的生灵,这一切简直就是天作之合……”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王斐还是个孩童的时候,他的父亲常会带他一道远游西安、成都、昆明和北京等诸多历史名城。父子俩时常会花上几个小时徜徉在博物馆和美术馆。形象生动的古代文物在王斐的脑海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王斐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回忆说:“我在圣殿中仰望汉人的面孔,就连作为奴仆的跪俑都是那样的矜持凝重;我看隋人面孔的庄严冷骏,凌人冷酷之美让人不敢正视;我更忘不了唐人面孔的轻狂不羁和宋人面孔的闲愁儒雅,但这些自信和精致的神情与质感似乎不再能从当代中国人的面孔中被找到了……”。从这样的言语中我们不难发现王斐画作的内涵:他们是关于逝去的一切,而不是过去本身。在这些诡异而优雅的作品中,通过近乎狂热的造像式细节重复,不时出现的强烈色彩冲突,以及既愤怒却又克制,以及无尽忧伤的交融,王斐的作品试图从环境自身来一探中国人精神失落与消逝的究竟和诱因,而他所采用的形式和语言特点都源于那个消逝的文化。他的作品就是献给那个消逝世界的挽歌。 在王斐2006年完成的最具代表性的《借我七百年》系列中有一幅主人公身体向右的作品。画面中的衣冠人物身披汉人的长袍,长发飘逸,头上结着中国汉人的发髻,他占据了整个画面的前景。他的长袍从画布的左下角一直延伸到右上角,与前倾的身体和俯视的面孔融合。他的左臂向下前伸,好象要靠在一块突出的山岩上,而他本身似乎也成了山岩的一部分。在他的身后,背景是若隐若现的山峰,让人不免联想到宋代山水。主人公露出近乎骨骸般的笑。黑色空洞的双眼凝视着他左腕上的四个小人。这些小人眼神空洞也近乎骨骸。其中一个是执刀的日本军人;另一个头顶着只有魔鬼才长的角,身上却长出天使般的羽翼;最后两个骑在一匹结实的草原矮种马上,一个身穿旗装,另一个编着蒙古人的辫子。显而易见,这四个小人在历史文本中代表着日本人,西方人,满族人和蒙古人。自十三世纪晚期元朝诞生以来,正是这些历史民族主宰了中国漫长而痛苦的历史。这个着汉人衣冠的人,他究竟是谁? 他是一种文明的化身,或用王斐的话说,是“汉人精神”的化身。我在王斐的画室(也许是一种巧合,王斐的画室就在北京一个普通塔楼的13层)看到的近作上,这一形象简直就是“霸占”了所有的画面。这些作品画幅多数都很大,而画面中高大的主人公姿态各异,从愤怒扼腕到静坐独思。他们衣袍上的蓝色斑驳 ,好象原始纯净的色彩已被时间洗刷过。通常,画面上主人公的体内会暴裂出数百个列成排,紧挨着的神情紧张忧郁的小人儿。有妇女,武士,儿童,贤士,用来寓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象《神思者》或是《我的城堡》这样的作品中,在主人公的胸前或是在伸出的手上可以看到一个赤身,蜷缩,阴郁的小孩,这也许寓指艺术家本人。通过这样的图画式的剧情以及主人公伟岸身躯的安排,王斐想让我们相信,这位汉贤,无论他以哪种形式出现,总在内心担负着国家的使命,承载着文化的命脉。虽然这中国汉人形象所象征的集儒家美德于一身的不二的君子,高贵大度而又睿智如刃,但自1279年宋朝衰亡以来“他”却从未成功挽救过中国人的尊严。王斐曾自言:“劝天借我700年回到那个古风失落的悬崖边,我想亲身聆听陆秀夫与其殉道者投海的哐哐巨响”,诚然,改朝换代是历史规律。但王斐在表白自己想“把中国人精神图腾的面孔拉回到700年前尊严失落前的那一刻,让他们在我的绘画世界里重新生长”时候,那么他肯定在失去的一切中看到了某些独特的地方。 无独有偶,“通过绘画为历史救赎”这一令人叹服的构想在西方也体现于格哈德•里希特著名的系列作品《1977年10月18日》就试图通过强迫观众面对上世纪70年代左翼恐怖的遗留问题和这些问题背后的极端思想体系以及支撑这一思想体系的理由,(简言之,在是要“经济增长”,还是要“充分重视法西斯罪行的问题上”,欧洲的统治阶层选择了前者。换言之,消费文化带来的不确定的繁荣是以牺牲历史公正换来的。)来重新唤醒历史意识。但王斐这位中国艺术家的图腾式概括最终还是打破了他与像里希特这样的西方画家的审美比照。里希特画出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原西德左翼组织领导人古德古顿•恩斯林的尸体,而王斐作品中承载“汉风”的神却是中国汉人精神的集体群像。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一种挥之不去的不安:尽管受到试图祛除历史之痛的愿望之驱使,王斐的作品形象更像生活在一个永不屈服的神话和想象世界里,是具体史实所无法企及的。也许这正是作为提纲挈领的一种自然禀赋,想象力是惟一可以抵御历史蜕变的力量。 但究竟如何通过视觉艺术表现出这种抗争呢?毕竟,通过历史比脱离历史找寻出路更难。也可以换种问法,作为一个国家和一种文化,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对她的孩子们都做了些什么?他们现在又是何种生存状况? 在2005年完成的一组震撼人心的画作中,王斐为我们指向了一个答案。这组名为《步人甲:步人甲之游牧入侵 步人甲之核子时代 步人甲之海洋威胁》的作品完全是用浅橄榄灰色完成的,令人不寒而栗。在所有这些作品中,汉人的化身不再是身着汉人长袍,而是披挂着各个历史时期的甲胄,且怒口大张。在组画中间的那幅《步人甲之核子时代》中,他站在一堆骨骸上,骨骸上都插满着导弹。实际上,除了几只愤怒上指的手外,他的整个身体都是由导弹构成的。在《步人甲之海洋威胁》中,汉人的化身像希腊神话的擎天神阿特拉斯一般肩扛航空母舰。甲板上两只巨蟹在它们的介壳中伺机而动。王斐凭借想象将汉人的化身转变成为国家通过发展军力寻求提升国际地位的一个鲜明的形象。这也许是当今中国人对“失去的尊严”所产生的一种症结。王斐在其他的作品中也对“失去的尊严”所产生的影响深表惋惜。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当然也寻求同样的地位,但这一点另当别论。在传统的中国儒家看来,圣贤不可屈尊。然而在王斐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这种似是而非的视觉评判:当今中国比过去几百年要太平得多,然而,其主流民间情绪却处处彰显着尖刻、不安和焦虑。公众谈话中既充满了狂野的民族主义色彩又对任何所谓的“反华”言论保持极度警觉,甚至人们会担心来自海外的神秘威胁。克服这种精神分裂式的文化心态的方式也许正是王斐想要在作品中表达的那种英雄化的并梦回唐朝武士式的“自信,自尊,和与生俱来的优雅”,这也就难怪他曾感叹“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了。 王斐的作品表达了痛苦的存在主义之父克尔凯郭尔式的真谛:人生,无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从个人角度来看,守望未来的同时却又不得不逆向的理解过去。克尔凯郭尔将人的存在描述成三个不同层次:感性、理性和宗教性。感性的人或是享乐主义者、或是热衷于生活体验的人,他们主观而具创造力,对世界没承担和责任,人世间对他充满着可能;理性的人则是现实的,对世界充满承担和责任,清楚明白人世间的道德、伦理和约束。因此,有别于感性的人,理性的人的世界观中充满著不可能与限制。面对不可能,理性的人就只有放弃,并永远为失去的东西而悲伤。这个时候,人只有凭借“信心的一跃”进入宗教性,相信在无限的神性中凡事无不可能,就算理性上明知事情之不可能,但也往往只有信仰的“荒谬”,才能使人重获希望。王斐是一位理想主义式的画家。他的理解方式是关于历史文本的,神话与宗教仪式感的,象征和虚拟的,空想的和理想化的。利用这些形式,他的作品探究着一种与自身精神源泉断割的文化的耻辱。这种文化似乎难以扭转通过“仅仅模仿西方,盲从日韩时尚”来重复几百年前的历史的命运。但在“汉人精神”与世断绝的境遇中,我们也同时看到了现代城市人的孤独无助——漂泊不定、麻木、极端失落后的空虚、对盛行的金钱地位至上思想的怀疑等等,在一个真假混淆,充斥着“假大空”的世界上踽踽独行。从多种角度来看,这正是我们为历史付出的代价。 在艺术想象力的深处,王斐的作品已估量出了中国所付出的代价。尽管从实际意义上看,失去的一切似乎已无可挽回,但他的作品仍发出寓言家般的抗争的吼声;他仍在不遗余力地寻求阻止象征着汉人精神的世界的消逝,在他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这种精神很感人。 在王斐的画室里有他饲养的20多只各个品种的龟,有两只从他十岁到现在,已经跟随了他十八年,在中国,龟是不朽和长寿的图腾,正是中国人在它的背上刻下了中国最早的文字。它也用来占卜。王斐饲养的乌龟们探出头,谦和地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无论是关于审美还是文化;画家本人也无时不刻牵挂着这种有血有肉的生灵,这一切简直就是天作之合。 看来,要让一切象征变得有意义,人文关怀始终必不可少。 Tully Rector(英国伦敦大学艺术哲学博士) 2007年6月于北京#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