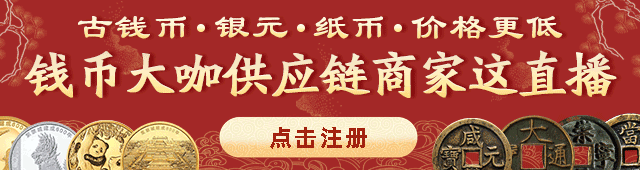杜大恺:用水墨画欧洲
一直想用水墨画画欧洲,经验了才知道并不容易。语言是有对象的,这成就了不同形态的艺术,欧洲人画油画,中国人画水墨,都有缘故,而不是心血来潮,凭空蹈虚的结果,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我想到这些。
从欧洲回来,我仍没有找到用水墨画欧洲的方法,二十五天,四千公里,其所见所闻显然都需要另样的面对。一路都是沿着地中海行驶,三个国家在城邦时期都是希腊、罗马的领地,有同一文化渊源,历史衍化出的差异并未泯灭其共同性,一色的蓝天、碧海、红瓦、绿树,一色的明媚清丽,闲适恬静,徜徉其间,有一种难以际遇的舒畅和轻松。
相同并不排斥差异,大而化之,西班牙或多一份奔放,法国或多一份浪漫,意大利或多一份热情,不是地理赋予的,而是人,人的行为以及人的行为的结果给你的印象。同是屋顶,会有朱红、绯红、橙红的区别,深深浅浅都释放出不同的情感倾向;同是墙壁,有鹅黄、豆绿、湖蓝、粉紫、珠绿、赭红,加上不同的并置与对映,会呈现不同的氛围;街区、阳台、窗沿、栅栏内外的鲜花却是一样的香艳,最令人驚异的是百叶窗的颜色,其色彩的奇妙会使你称绝。还有一式的阳光和清风,一式的白哲、金发、精于穿戴的男男女女,一式的熙熙攘攘的集市,一式的举着一杯咖啡或一杯啤酒在街道两侧浅斟低酌的游客,一式的仰面横在海边沙滩上享受阳光浴的青年、老人和孩子,一式的横七竖八架设在屋顶上的电视天线,……我不再一一叙述了,在没有边境检查,而我又无法辨识语言与文字的国别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一直行走在一个国家,薰衣草、橄榄树、葡萄园、向日葵一路伴你同行。所有这一切对于水墨画都是陌生的,如何把这些转移到你的画面上我没有凭藉。欧洲是最不缺少艺术家的一片土地,在欧洲的艺术中我曾经千百次地看到同样的人物,同样的景致,它们诚然是可以凭藉的,但我对将他们作为凭藉心存顾忌,我怯于成为他们的复制者,我期待用水墨画出一个中国艺术家眼里的欧洲。语言固有对象,但因为不同的面对,或应生成不同的语性,虽然很困难,但我不想退缩,我愿意面对。
中国人用油画画中国的人与风景已经有一百余年,进入新世纪似乎才渐渐画出一些本乡本土的味道,而用水墨画欧洲似乎还没有开始。清朝末年,一些欧洲的传教士曾经用油画、水彩、版画画过中国,但似乎并不成功,他们把中国漫画化了,我不想成为他们的后继者,异国或是异乡,他们那里也有堂堂正正的人生。
我相信有距离就有张力,空间的距离,时间的距离,以及弥漫其间的文化的距离,虽然遥远,但都可以亲近。水墨背后并没有民族主义的阴翳,它能够面对世界,也应当面对世界。
我最终还是画了一些,是不是画出了异国情调,是不是还维繫了水墨的韵致,亦只能任人评说了。我答应自己,倘有机会我还会再去欧洲。
- 上一篇: 黄龙玉产业的初始乱象和解决之道
- 下一篇: 私人收藏大热艺术品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