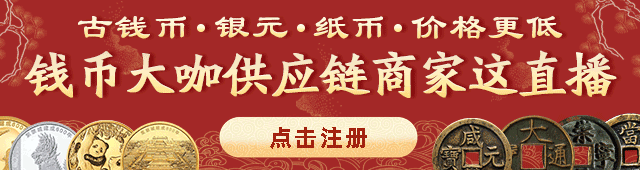古书画反潮流实践十九问
编者按:这是三年前《都市风》杂志对刘九洲先生的一篇访谈录,我们发现文中有关学术、鉴定、收藏的一些问题,与我们听到的这个方面的常识,有较大差异,但是刘九洲先生已经用他的收藏、学术实践,获得了各方面承认,因此,我们请刘先生将此访谈,补充一些新材料,再次刊出。
记者:刘先生您好!2008年底,您参与编辑的《宋画全集·欧美卷》出版,2009年底,您的专著《重现》出版,2011年底,您在匡时推出的《千载》拍卖专场,获得了很好的成绩。您作为学者、鉴定家、收藏家的身份,被很多人认为是跨领域的,很少有人在您这个年纪做到这一点,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能否介绍一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书画研究的?
刘:我先回答后面一个问题,在1991年考上大学之前,我一直在淮阴读书,1996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进入上海文汇报当记者,五年以后,去美国,从那时开始,算是专职从事中国古代绘画的收藏与研究。我接触书画还是很早的,9岁时候在爷爷的引导下开始学书,13岁时候,自己开始感兴趣,18岁读大学之前,我的书画类图书已经有11箱了。
关于跨界的问题,我是这么看的,我是为了鉴定,才去搞学术研究。而学术进步,就是发现了新知识,自然带动了鉴定进步,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或者比别人领先两三年,看到机会,自然可以把收藏做好。鉴定水平提高了,收藏才会提高,如果鉴定不领先,那么收藏的优势也就没有了——在收藏领域,要么拼资金,要么拼知识,没有第三条道路。从实践过程来看,打个比方,学术是结网,鉴定是寻找目标,收藏的过程是撒网。这个过程,是很自然的连续动作。
记者:您毕业于几乎是中国最好的新闻学院,毕业后进入最重要的新闻媒体之一,但是您却放弃新闻行业,转向书画,一般人可能觉得“书画”与“玩物”很接近,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刘:2006年秋天,我在浙江大学编辑《宋画全集》的时候,一个中国美院的鉴藏专业的同学来实习,问了一个很出乎意料的问题:“我们搞这些书画研究是在为啥”?我想了一下,回答说:“任何一个民族兴起,都会重新评价自身的历史,中国艺术史研究就是中国文明史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好中国艺术史,就会在文明传播、竞争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仔细想来,书画在离开古代历史以后,就不再是“玩物”,也不仅仅是“自娱”,更加重要的在于,这是国家力量的一个部分,和钢铁、汽车的生产一样,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当我多次出入密歇根大学艺术史系图书馆内,看到西方艺术是图书大约至少20倍于中国艺术图书的时候,当我看到西方重要博物馆的规模和运作模式的时候,当我看到西方艺术品一次又一次出现高价的时候,我感受到这种“文明力量展示”,是激烈的世界范围内的竞争。艺术史研究,完全不是“玩物”。
记者:艺术史这个词汇似乎很少用,中国多用“美术史”。
刘:美术史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概念,更加强调平面化,不少院校采用“史论系”这个说法,似乎还强调“史论结合”,这个说法让人感到有些困惑,因为艺术史是学术,“论”如果指的是“艺术评论”,那就不是学术了,评论更加接近新闻行业。所以,我倾向采用艺术史的说法。
记者:您在美国学习中国艺术史,但是,很多人以为学中国艺术史当然应该在中国,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刘:这个问题我其实碰到过很多次,大约是说,中国人强调笔墨,外国人不懂,能学到啥?一些外国学者研究中国艺术,受到这一类的质疑更多一些。其实,中国人互相之间,很多时候也互相指责“不懂笔墨”,这就把“笔墨”变成为一笔糊涂账。要论证外国学者“不懂笔墨”,首先不能认为中国学者“全部懂笔墨”,应该建立一个检测模型,通过这个模型的考试,把中国人中间不懂笔墨的找出来,这样,再把这个模型用在外国学者身上,看看他们是否懂笔墨,这样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过程。世界各地都有滥竽充数的专家。#p#分页标题#e#
对于绘画来说,尤其是早期绘画,体现了一种绘画艺术走向成熟期的过程,采用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非常合适。相反,采用“笔墨”去研究早期绘画,倒未必适合,已经有著名的《溪岸图》的例子,反向证明了这一点。从总体上看,西方学术界一直强调学术标准,强调“可检验的研究”,强调论文的严格标准,这些措施,恰恰可以把“艺术心学”,以及滥竽充数的研究者剔除——西方科学哲学指出“心学”类似于神学,不是学术。
记者:您个人的学习过程是什么?
刘:主要是尽可能掌握全部资料,多看论文,看看学者互相之间如何讨论问题。再一个就是把学来的知识不断运用,主要就是在拍卖行看到一些不懂的作品,就去想方设法研究,积累很多次“案例研究”以后,研究就变得很轻快了。一开始我采用的方法、材料也很笨拙,后来就越来越快了,也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不断研究新材料,是进步的最快通道。
记者:学好艺术史,就可以到市场上买东西吗?
刘:您事实上在询问艺术史与鉴定的关系。艺术史目前有三个主要方向,一个是研究图像关系的,这是传统的主流方向;第二个是以文献研究为主体的,这是中国宋以后经常使用的办法,唐宋艺术史学者并不这样做学问;第三个方向,是做艺术品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这个方向也有数十年积累了。与鉴定最接近的是研究图像关系的艺术史,艺术史与鉴定的关系,大约是一种练拳与打架的关系,不练拳,打架肯定不成。但是不是说,你在家里练拳十年,出江湖就一定能打赢人家。因为打架遇到的复杂情况,远不是练拳时候可以准备的。有一些专家,完全是从书本上,看前人打架记录,就以为自己会打架,这是很危险的。
记者:那么除了艺术史方面的训练,还需要什么方向的训练呢?
刘:艺术史告诉你一个综合概念,告诉你常规是什么样子,也就是“中庸”是什么样子,中庸不是捣浆糊,而是天平中间那根杆子,你上来就抓不住中间,抓不住常规,那一定要吃苦头的,但是,日常鉴定,则主要是面对异常。
譬如说,董其昌一般是啥样子?艺术史可以举出一些代表作来,让你知道这些基础知识。但是董其昌异常在哪里?异常在于,他大约具备很多种书法倾向。这是一般书法家不具备的,也是任何艺术史都没有谈到的。这种异常状况,导致你想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超乎寻常的资料积累。王铎的例子呢?王铎常规研究目前做得很好,异常在哪里?王铎在54岁以后,出现了几个很好的代笔人,使用真印章。这就导致王铎晚年书法的印章比对方法几乎无效,这就是王铎鉴定中需要注意的“异常”。很多人会感兴趣问:“宋画中的异常”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往往忽视了宋代绘画走向成熟时期(北宋前期)的多种特征,这恰恰是宋代绘画中最珍贵的部分。历史感不强的人,往往被南宋大量绘画淹没了。这就是宋画研究中的异常。
记者:如何学习才能面对这些“异常”呢?
刘:还是谢稚柳先生说过的,先认真研究一家。把一家研究透了,注意到各方面问题了,在其他研究中,才能有警惕感,才能发现异常状况。从1990年开始,我大约花费了10年时间,研究林散之书法,现在想来,作为入门研究,这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因为林散之的作品很多,水平也高,变化也很多,后来作伪的东西也很多,市场上可能遇到的问题,在林散之书法这个领域内,或多或少都发生过。这样就会触类旁通。
在研究一家之后,还需要对新问题存在敏感度,出现异常作品的时候,要比较周密地考虑有哪些可能性,对一般人认为反常的事情,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要保持警惕,这样不断训练,就进步了。
- 上一篇: 尹毅:也谈“打造”画派
- 下一篇: 舍一画而谁耶--读张诠的画